赵振杰
在当代众多少儿类图书当中,以人与自然关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可谓恒河沙数,然而真正能称得上是“生态文学”的作品却是凤毛麟角。何为“生态文学”?用批评家吴景明先生的话讲:“真正的生态文学应当是‘诗’(诗化的文学语言)、‘思’(作家对生态意识的思考——文学的社会功用价值)、‘史’(反映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三者之间的交融与互渗,而不应偏废任何一方。”

纵观浬鎏洋的大自然文学作品,多是讲述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等北方少数民族与动物与自然的故事,而且是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集中展示,以及对于“人与动物和谐共处”主题思考上更加系统与深入,真正实现了可读性、艺术性、思想性的完美融合。

作者浬鎏洋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下乡后又转乡到鄂伦春自治旗的诺敏乡。曾先后担任过鄂伦春自治旗文化局长、旗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长期致力于以大兴安岭森林民族民俗风情为题材的研究与创作。“深入生活、扎根沃土”的创作理念,及其持之以恒、甘之如怡的地理和人文考察,使得他可以从民族学、社会学、生态学、人类学等多个角度,对当地的文化历史进行深入描摹与探讨。他的创作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主题范畴,而且为其还原了一种原初意义上的精神风貌。他的作品视角独特、结构严整、内容丰富、情节跌宕、形象饱满、思想深刻,集描写、抒情、叙事、议论与一体,称得起是“中国最美大自然作家”,“生态文学先驱”“大自然诗人与文人”普里什文的精神继承人。

在浬鎏洋的眼中,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就是其文学创作的丰沛源泉。在文中,他毫不吝啬地运用大量笔墨为读者建造了一个童话般的自然王国:在那里有春草蓬勃的原野、夏花烂漫的远山、秋叶金黄的树林、冬雪皑皑的湖畔,真可谓“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在那里还生存着憨态可掬的大黑熊、活泼可爱的小狍子、五彩斑斓的蝴蝶、温驯善良的马鹿、优雅端庄的天鹅、双宿双飞的鸳鸯……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世界。正如著名评论家包明德的评论所言:“浬鎏洋对语言的色彩和音韵非常敏感,且很有分寸感,他的每一篇小说都闪耀着诗歌的文采,每一个字都打磨得闪闪发光,充满诗情画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采用动物的视角来展开叙事,使作品产生出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

人与自然如何共处”这一生态学意义上的核心命题: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还是自然的一分子?或者说,人类是自己的主人还是欲望和野心的附庸?这的确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作者巧妙地以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为背景,用小动物的视觉来展开叙事,以纪实与拟人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原汁原味地向我们展示出大兴安岭这个神秘王国里,演绎着的动物与自然、动物与动物、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生动而又传奇的故事。其中,既有对该地区自然地貌和各类动物生存状态的生动呈现,也有对那些尚未被现代文明冲击的少数民族淳朴生活与风俗习惯的集中展示,还有对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性、官方与民间、自然与人类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度思考与勘探,不啻为一部部“自然景观的生动画卷,民族风情的梦幻交响,绿色生态的优美颂歌”。

严格意义上讲,单纯以“儿童文学”来定位浬鎏洋的大自然文学是不够准确的。虽然,出版社明显是以“儿童文学”的思维方式来设计、出版、推介,然而,就其所有作品所蕴藏的极为丰富、复杂的思想内涵而言,该大自然文学作品是狭义的“儿童文学”所无法涵盖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价值观的立体多元呈现。作者没有提供廉价、简单的“善恶分野”,而是试图告诉孩子们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场上,善与恶、对与错、是与非、美与丑……这些价值判断会发生奇妙的变化,甚至于截然相反。例如,对于狍子、野鸭、灰鼠、马鹿等大自然食物链底层的所谓“弱势群体”而言,貂熊、金雕、野狼、土蛇等具有攻击性的“危险动物”天然的被视为“邪恶”的化身,然而,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它们的立场上去观察与思考,我们便会发现,它们也有情感、有温度、有智慧、有灵魂。为了生存,它们敢于铤而走险;为了儿女,它们甘心赴汤蹈火;为了荣誉,它们不惜舍命捍卫;为了爱情,它们宁愿肝脑涂地……

其次是揭示出大自然的波诡云谲、瞬息万变。对于儿童而言,大自然不仅仅只意味着纯净的阳光、潺潺的河流、蓬勃生长的树木、鸟语和花香,还有电闪雷鸣、森林大火、洪水猛兽、弱肉强食。因此,在作品中,浬鎏洋的笔触既有柔情
似水、和谐圆融的一面,例如,他这样描写山林中的季节:“春天的大兴安岭,是多彩多姿的美丽世界。江河开始解冻,清清亮亮的河水闪动着流光。山坡上雪还没有化尽,人们都说这是乍暖还寒的时节。就在这春寒料峭的山林里,春姑娘早已悄悄地踏遍了大兴安岭的山坡,在那儿撒下一片片瑰丽的彩霞——映山红,在冰雪中迎寒怒放。”同时,他也有金刚怒目、沉郁顿挫的一面,例如,他这样描写突如其来的森林大火:“这时的森林处在一片恐怖之中,五花八门的野兽叫声,狂风的怒吼声,大火中噼里啪啦的燃烧声响成一片。各种动物都被大火赶了过去,它们已忘记了相互残杀,只顾各自逃命了。”

另外,作品中渗透着浓浓的普世关怀和“类宗教情结”。例如:小猎手莫日根特,在失去父母之后,重新振作起来,在与大自然界形形色色动物的亲密接触过程中渐渐产生出难以割舍的感情,进而萌生出要建造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动物乐园”,在那里没有厮杀、没有伤害,万物和谐共融,彼此成全。一切都基于莫日根特在与动物的朝夕相处中天然生成的朴素人生观、价值观:“这美丽的大自然,应该是所有生命共享的,所有的生命也应该是平等的;而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的扼杀,都是一种自私、一种邪恶,是对生命的亵渎。想到自己以前的行为,我有一种罪恶感、愧疚感,对自己过去捕杀动物的行为有一种深深的自责。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活出一个真正的自我。”正是在这种普世关怀的指引下,小主人公莫日根特渐渐生出一种类宗教意义上的“普度众生”的情结。这不禁会令读者联想到《旧约圣经·创世纪》中那个著名的“诺亚方舟”的神话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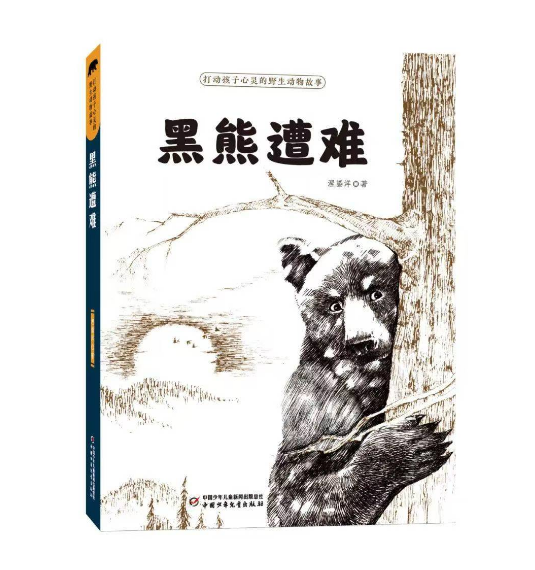
而在对黑熊的描写中,作者浬鎏洋则着力呈现出大兴安岭少数民族与黑熊之间的共存之道——对于鄂伦春猎人、鄂温克族牧民而言,大自然界中万物有灵、草木皆神,应当心存敬畏、心怀感恩。如果说大兴安岭的黑熊是守护大自然的野性力量的体现,那么原始部族猎人就是维护森林繁荣的人性力量体现。小猎人作为原始宗教信仰和草原朴素生态主义的继承者,其生态人格已自觉体现在信仰和行动当中。他们敬畏图腾,善待黑熊,尊崇狩猎规矩:遇上熊不能打;怀孕的母兽不打;哺乳期的母兽和兽仔不打;正在交配中的野兽不打……可以说由黑熊和原始部族构成的生态系统正是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长久繁荣的根基。此外,小说在呈现原始部族生存智慧的同时,还穿插讲述了诸多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其中涉及原住民的建筑、歌谣、舞蹈、绘画、美食、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等等,给读者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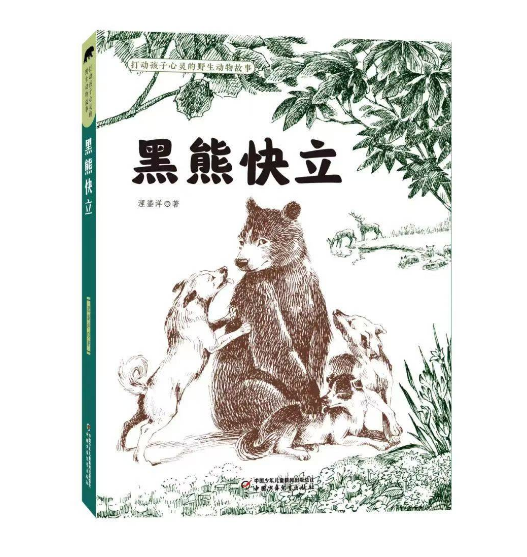
与多数同题材作品不同,浬鎏洋的大自然文学系列,不仅仅揭示了生态危机,表达生态焦虑和控诉不法行径,而且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从他的有关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作者将希望充分地寄托在科技文明的发展与革新之中,为此,他还饱含深情地在文本中建构了一个极具科幻意味的大兴安岭生态乐园,在那里,黑熊家族以及其他动植物能够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在那里,原始部族的生活方式、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得以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在那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可以变得更加和谐、圆融。虽然仅就当前的生态现实而言,小说中这一情节多少还带有些浪漫主义幻想色彩,但其中所传达出的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情怀却是弥足珍贵的。起码,浬鎏洋先生真诚地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众生平等,万物共生”的理想最终会借此真正实现。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如果用狭义的“儿童文学”来框定浬鎏洋的作品,显然是不够恰当的,因此,在这里,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大自然文学作品”。即便是退一步讲,将这些作品勉强归入“儿童文学”的论域范畴中,我们也可以通过类比显豁地看到,浬鎏洋的“大自然文学”系列,称得上是儿童文学中的出类拔萃的“这一个”,它所具备的开创意义和独特品质,注定了它最终要从众多的“这一类”之中脱颖而出。
某种意义上讲,浬鎏洋是超前的,在一个以过度开发自然为基调的时代,他能够抵挡住种种诱惑和压力,把自己柔韧的美学触角潜入文学世界的原初和根本,这使我们深切地感觉到,他仿佛是一个生活在时间之外或世界开端的“抒情诗人”,用其手中的生花妙笔将“大自然”转换成可以承载更多文化与思辨的精神容器;他试图恢复自然的本来面貌,从而使自然真正成为既诱人探寻,有永远无法穷尽的永恒;他使我们由衷地相信:对于自然的需要,不仅因为那里有久违的阳光、流水,以及茂盛的树木花草,更因为那里有越来越难以触摸到的人类根脉,有一种别样的人生意境。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以大自然野生动物的名义,再次呼吁: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希望更多的人,尤其是像我一样的青年人,能够走进自然、贴近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用真心去感受大自然的野性,倾听大自然的呼吸,用实际行动去探寻和捍卫我们每个人自己心目中的“桃花源”。
(赵振杰, 著名新锐文学评论家,文学博士,现供职于河北省作家协会,河北文学馆副馆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文学评论文章散见于《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文艺报》《小说月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刊物。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人民文学》“近作短评”金奖等。)


